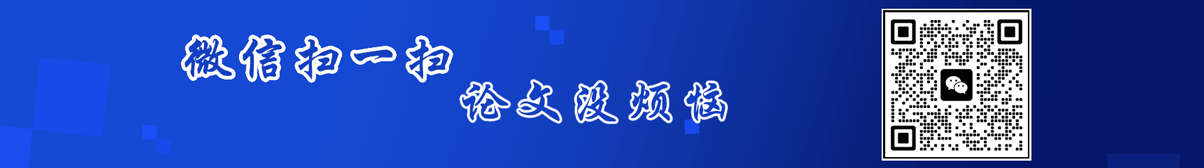文学与爱情主题论文范文:对爱情文学与文学中爱情描写的美学探讨
一、爱情在文学中的地位
莫达尔认为:“诗与文学的伟大便在于性爱,因为生命中性爱占重要成分,这些文学因此对生命便更真实”,“若不叙述爱的兴趣,文学便简直不能存在”。(1)弗洛伊德也说:“造成‘恋爱’的条件是什么?或者说,男人和女人根据什么选择自己的爱恋对象?当现实生活中找不到合乎自己理想的对象时,他们又是如何来满足自己的要求的,这一向是一个由诗人和想象力丰富的作家们描述和回答的问题。”(2)在看重性本能作用的弗洛伊德那里,艺术作为人类的高尚活动之一是作家性欲的一种转移或升华,“性的冲动,对人类心灵最高文化的、艺术的和社会的成就作出了最大的贡献”。(3)爱情是文学中最重要的意象和主题之一,从《诗经》中的《关雎》、古罗马奥维德的《爱的艺术》,到薄伽丘的《十日谈》、曹雪芹的《红楼梦》,再到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曹禺的《雷雨》,等等,古今有数不胜数的描写爱情的文学作品。
爱情在文学中的重要地位是与爱情在人生中的重要地位相关联的。马克思认为,男女两性关系的演进是人类文明演进的标尺,“人和人之间的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是男女之间的关系。在这种自然的、类的关系中,人同自然界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同自然界的关系,就是他自己的自然的规定。因此,这种关系通过感性的形式,作为一种显而易见的事实,表现出人的本质在何种程度上对人来说成了自然界,或者自然界在何种程度上成了人具有的人的本质。因而,从这种关系就可以判断人的整个教养程度”。(4)马克思注意到爱情中的悖论,即一方面含有动物性,另一方面又含有人性、灵性甚至神性的成分。按照李泽厚的解释,爱情是“自然的人化”中情欲的人化,“性欲成为爱情,自然的关系成为人的关系,自然的感官成为审美的感官,人的情欲成为美的情感”。(5)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在其名著《或此或彼》中探讨了爱情。他认为,爱情是人内心自然产生而不可抵挡的一种必然性力量,它诉诸于个体的感性肉欲,因而具有瞬间性和直接性,是必须得到满足的。他把爱情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一种欲望还没有完全醒来而只处于那种最初懵懂的原初阶段,这时的欲求还没有具体的对象;第二阶段是一种欲望开始醒来,所欲求的对象具体出现在眼前的情窦初开的阶段;第三阶段是真正的直接爱情阶段,爱的力量与心灵感受连成一体。这种爱不是纯粹的感性肉欲,而是在精神上赢得对方的爱,唯有在精神上获得对方的爱,爱情的使命才告完成。这些说法都说明了爱情的两面性。
爱情在文学的创造和阅读中也起着重要作用。马斯洛认为,包括文学艺术活动在内的人的高峰体验与爱情及性活动有关,“这些美好的瞬间体验来自爱情,和异性结合,来自审美感受(特别是对音乐),来自创造冲动和创造激情(伟大的灵感),来自意义重大的顿悟和发现”。(6)作家、艺术家是感情生活丰富的群体,他们对爱情的观察更富有感性色彩。司汤达认为:“爱是一种快感,是在尽可能亲近的接触中凝视、抚摸,以一切感官体会一个爱着我们的可爱的人儿从而得到的快感。”(7)在他眼中,爱情是一种刻骨铭心的经验,一种难以忘怀的记忆。20世纪初,法国诗人阿波利奈尔在他的诗作《米拉波桥》中,虽然发出“爱情象这泓流水一样逝去∕爱情逝去∕生命多么缓滞∕而希望又多么强烈”的慨叹,但他还是用诗歌记录下他与少女玛丽·罗朗森“面对面∕手握着手”的瞬间。这说明,爱情不仅标志着人生理的成熟,也昭示着人心智的成长。爱情文学很多写的是当事人如何通过两性的交往获得对自我的认识。爱情文学真正的价值在于它真实细腻地呈现了人类可能具有的性与爱以及与之相关的诸多心理、社会元素纠葛冲突的状态,进而思考人类自然层面和精神层面可能具有的关联方式和跃迁潜能,因此爱情文学和爱情描写在塑造人性、创造人们对可能生活的想象方面具有独特的功能。正如我国学者柳鸣九所说的,爱情文学的“生命力不在于把爱情故事的情节写得叫人爱看,更不在于赋予男女主人公某些外在的价值,如美貌动人等等,而在于写出了人的感情、人的精神”。(8)弗洛伊德更是认为,爱情文学可以给人们一种被压抑欲望的替代性满足,“人们可能做得更多,可能试图再创造现实世界,建立起一个世界来取代原来的世界。在那里,现实世界中最不堪忍受的东西消除了,取而代之的是人们所希望的东西”。(9)
二、文学的爱情神话学
文学创造了两种不同类型的爱情神话学:浪漫的情爱和美妙的性爱。前者更重视精神层面,后者更重视肉体层面。就前一方面说,文学从不同侧面刻画了美满的甚至悲壮的爱情。北宋李之仪的词《卜算子·我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夜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书写了处于阻隔中的永恒之爱。同样,悼亡诗中的一部分情诗,也是在对爱情的追忆中祈求爱的永恒。苏轼的《江城子》把现实与梦境、悼亡与伤时相结合,表达了超越阴阳两界的真挚爱情,“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在文学对爱情神话的营造中,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是对浪漫的痴情之爱、炽热之爱的表白和对美好生活的想象,比如徐志摩的诗《这是一个懦怯的世界》:“披散你的满头发,∕赤露你的一双脚,∕跟着我来,我的恋爱,∕抛弃这个世界∕殉我们的恋爱”,“你跟着我走∕我拉着你的手∕逃出了牢笼∕恢复我们的自由∕那是一座岛,岛上有青草∕鲜花,美丽的走兽和飞鸟”。所以各民族有数不尽的爱情诗、爱情故事和小说就不足为奇了。当然,这其中最为感人至深的还是那些描写爱情悲剧的作品,从《孔雀东南飞》到《罗密欧与朱丽叶》、《少年维特之烦恼》等。爱情悲剧作品,尤其是描写为了爱而殉情的作品的独特性在于,它体现了弗洛伊德所说的生本能(性、食、自我保存)和死本能(回归无机体状态)的奇妙的融合。本来,爱情的自然根源是通过两性的结合推动生命的延续,但却由于门第、出身等造成的沟壑或种种不合理的干扰不能成功,于是当事人以自戕的方式结束生命去追求永恒之爱。在这里,生即是死,死即是生,爱情被提升到精神层面。
据研究,现代人对浪漫爱情的追求与浪漫爱情小说的爱情描写不无关系,女性尤其如此。“绝大多数女性不为吸引男性的那种色情描写所打动,从而引起性冲动。能迅速引起女性性响应的是动人的爱情关系,罗曼蒂克的爱情文学与艺术”。(10)浪漫爱情小说原本就发源于西方。瑞士作家丹尼斯·德·罗吉蒙在《西方世界的爱情》中考证,浪漫的恋爱是中世纪宫廷之爱理想的蜕变形态,其性质主要是精神之爱。我们可以从中世纪晚期流行的以颂扬“荣誉、爱情和忠诚”为主题的骑士传奇中窥见一斑,甚至在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中依然可以看到其漫画式表现。到了18世纪,英国的感伤小说以求婚和结婚为中心,把情感放在理性之上,赞美炽热的爱情,体现了男权制下女性的理想。西方现代的浪漫爱情小说则带有个性主义的叛逆色彩。埃里奇·西格尔的《爱情故事》就是如此。该书写的是美国金融巨子巴雷特三世之子奥利弗·巴雷特四世与出身于面包师家庭的平民女子詹尼弗·卡维果里之间的故事。二人共同就读于哈佛大学,他们冲破门第的壁垒和家庭的反对走到一起,宁愿靠自己的努力自食其力。在巴雷特四世事业蒸蒸日上之际,詹尼弗却不幸25岁时死于白血病,而巴雷特四世最终也获得了巴雷特三世的谅解。故事的编码非常切合美国年轻人的梦想。西方至今仍然存在许多模式化的浪漫爱情小说。阿多诺在研究大众文化时便指认“文化工业把爱情归结为浪漫史”。(11)他的判断着眼于资本主义社会大众文化中爱情书写的欺骗性。的确,无论是平民少女怎样获得富家子弟的钟爱喜结良缘的现代灰姑娘的故事,还是穷家小子如何通过个人奋斗取得事业的辉煌并最终赢得美女的芳心,大众文化的此类模式无疑会给读者提供神话般的满足。言情小说属于中国化的浪漫爱情小说,其爱情描写也是构筑了一个爱情乌托邦。港台言情小说家如琼瑶、岑凯伦、席慕蓉等人的作品,极写两性的痴情、纯情,精神之爱大于肉体之爱。言情小说后来有向悲情演化的趋势,比如痞子蔡的《我的第一次亲密接触》。言情小说虽然有多种模式,但大抵不脱离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套路。
与前面一种类型不同,后面一种爱情文学偏重于性,当然是健康的性。恩格斯曾经称赞德国诗人维尔特,认为“维尔特所擅长的地方,他超过海涅(因为他更健康和真诚),并且在德国文学中仅仅被歌德超过的地方,就在于表现自然的、健康的肉感和肉欲”。(12)恩格斯所说的“自然的、健康的肉感和肉欲”就是不少作家探讨的话题,这方面最为著名的作品当数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和杜拉斯的《情人》。劳伦斯向往着“性行为和性思想的和谐统一”。他认为:“在性和肉欲方面,我们的头脑是毫无进化的。现在我们要迎头赶上去,使对肉体的感觉和经验的理性意识与这感觉和经验本体相和谐,即让我们对行为的意识与行为本身相互和谐统一。这就意味着,对性树立起应有的尊重,对肉体的奇特体验产生应有的敬畏。”(13)劳伦斯视性与美为一回事,认为假使我们的文明教会了我们怎样让性感染力适当而微妙地流动,怎样保持性之火的纯净和生机勃勃,让它以不同的力量和交流方式或闪烁、或发光、或熊熊燃烧,那么我们就能终生生活在爱中,而对所有的事情都充满热情。小说《查泰莱夫人的情人》里查泰莱夫人(康妮)的丈夫克里福·查泰莱是一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去了性功能的自私而虚伪的实业家。康妮和看林人梅乐士由相识而相知,逐渐克服了性生活和婚姻的挫折感,在感觉和本能中体验健康的性爱,从肉体经验中感知思想的形成。杜拉斯的《情人》是以一个老年的妇人对初恋情人的回忆自传式方式展开,写的是一个情窦初开的法国少女和一个受了法国教育的中国青年男子在西贡的恋情。该小说的深刻之处,在于细腻地刻画了两个种族、肤色、文化传统和家庭背景截然不同的男女,在异性的相互吸引中体验原本属于自己的欢乐,无拘无束地继续生命的探求。在杜拉斯眼中,性的欲望不仅纯洁自然,而且具有让人获得自我、获得爱情的力量和美感。对于劳伦斯和杜拉斯这样的作家来说,人之超越动物繁殖本能的地方便在于性。性的描写被审美化,性的感知和性的快乐成为观察人之本性的最佳切入点。
三、性与爱情、婚姻、社会的纠葛
在传统意义上,性、爱情、婚姻常常是一体的。弗洛伊德说过,“在一般情况下,凡健康正常的爱情,需依靠两种感情的结合,一是温柔而执着的情,另一种是肉感的欲”。(14)然而我们看到在文学中,性与爱常常是分离的。茅盾在其《诗与散文》中把爱情比作诗,肉欲比作散文。前者“空灵,神秘,合乎旋律,无伤风雅”,后者“现实,丑恶,散文一样”。这可能代表中国作家认为情高于欲的一般性看法。的确,审美化的爱情与性欲常常是分离的,比如忘年恋就属于动人的情爱,而不是性爱。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中的母亲对老干部的单恋让我们体会到爱情的执着和纯美。艾米《山楂树之恋》中老三对静秋的爱也属于在“文革”这个特定的禁欲主义背景下发生的“纯爱”,即促使被爱的人一切愿望成真,而不求性的回报。同样,处于性无知状态下的静秋对老三的爱也只有纯情,缺少性的渴望。
事实上,不少文学作品正是通过描写性、爱情和婚姻之间的冲突获得了叙事的张力和人性的深度。例如,无论《雷雨》中的繁漪,还是《安娜·卡列妮娜》中的安娜,都是处在情性、妻性和母性的巨大冲突之中。当她们情性的一面萌动时,她们为人妻、为人母的责任担当就要与之发生龃龉,而她们动人的魅力恰恰就体现在冲决罗网的困兽犹斗般的挣扎之中。《包法利夫人》中的爱玛也是如此。爱玛身为乡间地主的女儿,自小在修道院接受了贵族式教育,读过不少浪漫的情感小说,耽于幻想,聪慧而机敏,而平庸、愚钝的丈夫查理·包法利“见解庸俗,如同往来行人一般,衣着平常,激不起情绪,也激不起笑或者梦想”。查理虽然忠厚实在,也很爱她,但与她想象中的具有“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启发你领会热情的力量、生命的奥秘、一切秘密”的梦中情人相距甚远,也与她“欢愉,激情,陶醉”的爱情生活想象差距甚远。可是她两次发生婚外情,均被情人所抛弃,最后被迫自杀。与之相反的例子是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中的娜塔莎。少女时期的娜塔莎单纯、浪漫,不谙世事,与安德烈公爵真挚相爱,但二人基本上处于分离之中。娜塔莎感情的火焰燃烧得太热烈了,以至于与库拉金私奔。在安德烈重伤身亡之后,和彼埃尔结婚,成了一个幸福、娴静的少妇。在娜塔莎身上,热烈、冲动的恋爱生活与稳定、平淡的婚姻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更高的意义上,婚姻与家庭又是社会关系的一部分,性、爱情、婚姻与社会之间常常发生冲突。而在描写这种冲突时,古典作家与20世纪作家的态度有别。19世纪之前,人们一般认为民族、国家大义重于个人私情,裴多菲的诗《自由颂》——“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可以作为例证。同样的例子还有司汤达的小说《伐妮娜·伐尼尼》,它描写意大利烧炭党人米希律里为了民族的解放毅然舍弃追求单纯的男女之爱而行告密叛卖之事的伐妮娜。而到了20世纪,作家们常常自觉不自觉地选择一种爱情至上主义甚至性至上主义。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描写了一战中参加意大利军队的美国人亨利从主动参战,到质疑“神圣、光荣、牺牲”这些字眼,厌恶以至逃避战争的心路历程,以一种凄婉的笔调再现亨利中尉与英国护士凯瑟琳的爱情悲剧。福柯更是令人信服地揭示了性与权力操控之间的关系,认为“性的动机——性自由的动机,还有人们获得性知识和有权谈论性的动机——其正当性是与政治动机的正当性联系在一起的”。(15)所以,王小波在《黄金时代》中便通过性的感官性和世俗性来挑战权力对性的操控。当人们硬把王二与陈清扬扯到一起,称无辜的陈清扬为破鞋时,王二真的与她发生了性关系,从而成全了陈清扬的破鞋恶名。然后,王二以露骨地展示性活动过程的“交代材料”满足了人们的窥视欲而得到领导的欣赏。作品以此讽刺禁欲主义的荒谬。
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金瓶梅》也描写了性与爱、情与欲的分离状况。《红楼梦》中贾宝玉和袭人有肉体的交欢,却没有爱。贾宝玉、林黛玉是一对心心相印、相知相爱的人儿,但是他们的情感尚且停留于互相试探的情的层次,没有性或欲的成分。诚如夏志清所说:“本来‘情’与‘欲’在实际上是相当难区别的,‘情’可能是‘欲’在某种文化势力诱导制裁下变相而产生的东西……但是畸形的情感,不健全的情感,在一个小说家看来,至少要比仅被本能欲望所支配的生活更饶兴趣。”(16)在很大程度上,宝玉对黛玉的恋情是一种童心未泯、冷暖相知的共享之情,它可以推及到其他女性甚至同性身上,“宝玉对众多女儿的普遍痴情,一开始就不是出于异性的吸引,而是出于对世故未涉、童蒙未开状态的一种留恋,对天真丧失的一种惋惜。这里面缺失或淡化了正常的性吸引”。(17)这是汉文化传统中试图将肉体欲望和精神相隔绝而形成的病态的“意淫”现象。与其对立的是《金瓶梅》,西门庆对众多妻妾只有动物式的性,而没有情。
20世纪以来,人们在重新思考性和爱、情和欲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在这里我们需要提到日本作家村上春树。他的贡献在于以艺术的方式证明了性爱如何大于爱情,性如何成为现代孤寂人群孤寂心灵的一种交往方式。在性氛围和性行为中,男女坦诚而敞开地展示自我。正因为村上春树把性作为人自然存在的真实一面来处理,性超越了爱情、婚姻、家庭、伦理,被表现得很洁净。例如,在《挪威的森林》中,渡边和直子、绿子、玲子的性行为都是自然发生的。村上春树从多个方面展示了男女两性在情侣关系之外情感上的慰藉和精神上的互补,“使‘性爱’从‘幸福恋爱—美满婚姻’的模式中解放出来,成为一种男女间日常的基本沟通渠道和交往方式,一种让人们彼此更亲密、体贴、深层理解的交流方式”。(17)从而使人们对性、爱情及两性之间的关系有了全新的认识。
四、错乱的爱情
与文学所创造的幸福美满的爱情神话相比,文学的爱情书写似乎对扭曲、痛苦和不幸的爱情生活更为青睐,性虐待狂、性受虐狂、色情狂、厌女症得到了触目惊心的表现。在《金瓶梅》中,西门庆喜好以在女性下体烧“香瘢”的方式满足自己病态的占有欲,而与他交欢的女性也乐意被这样做。在《挪威的森林》中,英俊潇洒的永泽缺乏对待爱情的严肃性,生活轻浮放荡,随意与女子发生性关系,对真爱他的初美也不知珍惜,致使初美自杀。瑞典作家斯特林堡与他第一任妻子的婚姻充满猜疑、对抗和由不同的出身、生活方式而产生的矛盾,所以他的传记以《地狱婚姻》来命名他的这一段爱情生活。书中斯特林堡发泄了由这段爱情所触发的对所有女性的偏见、不满与仇视。
在文学中,我们常常会遭遇生活中难得一见的变态的错乱的爱情:姐弟(兄妹)恋、母子恋、父女恋以及同性恋、恋童癖等。弗洛伊德认为,乱伦是人类一种巨大的性诱惑,“人类对于性的对象的选择第一个常为亲属,如母亲或姊妹,要防止这个幼稚的倾向成为事实,便不得不有最严厉的惩罚”。(18)法国作家萨德在其作品中描写了一系列变态性行为:同性恋、性虐待狂、乱伦等。在小说《欧叶妮·弗朗索瓦》中,与女儿有染并谋杀他视为障碍的妻子的弗朗索瓦辩称:“美的力量,爱情的神圣权利,绝不理会无聊的人为的习俗,爱与美的影响扫除了陈腐的规矩,像阳光清除笼罩大地的茫茫夜雾。”因而萨德的作品几乎成了各种性恶习的展示。纳博科夫的《洛丽塔》某种程度上集恋童癖与乱伦于一体,写的是年过四十的中年男人亨伯特对他的继女——年方12岁的洛丽塔的畸形恋情。亨伯特认为9岁至14岁的性感少女有一种特有的优雅与纯真,他童年时代在法国海边与早夭的阿娜贝尔有过朦胧的恋情,这时候的洛丽塔就成了执意寻找天真的亨伯特眼中阿娜贝尔的替身。所以在很大程度上他爱上的不是真实的洛丽塔,而是想象中的洛丽塔。真实的洛丽塔表面上以顽皮而率直的少女面目出现,其实早已浸染了美国文化熏陶下的成熟与世俗,不仅会巧妙地在母亲与亨伯特之间周旋,把亨伯特玩弄于股掌之中,而且年少失身,知晓性事。在亨伯特踌躇于道德的负罪感与她做爱时,她却乐于充当他的导师。文学对性禁忌的突破无疑触及了人性中最为隐秘的未知领域,从而使人类光怪陆离的内在情欲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按照精神分析学说,人们很可能把对母亲的爱转移到最像母亲的姐妹或姨妈身上。拜伦爱同父异母的姐姐,华兹华斯、雪莱爱他们的妹妹。这些情况虽然未必导致事实上的乱伦,却无疑激发了他们诗歌创作的灵感。从《忏悔录》看,卢梭对比他大十多岁的贵妇人华伦夫人的爱也伴有浓厚的恋母情结。从小受过多位女性庇护的卢梭对华伦夫人有很强的依赖感,彼此之间也以“妈妈”、“孩子”相称呼。秘鲁作家巴尔加斯·略萨甚至以自己和姨妈胡利娅的真实情感经历为素材,创作了小说《胡利娅姨妈与作家》。略萨虽然不赞成错乱的性行为,捍卫情欲的纯洁性,但“认为人类有权享受情欲,情欲的种种变化和差异应该受到尊重和保护,因为这与人性的复杂性有关系”。(19)他试图揭示人类本能的丰富性、真实性以及探索者的巨大力量。这类文学是作家按照某种内心的秘密组合世界,使人们在幻想中拥有他们过不上的生活。
爱情文学尽管描写了诸多错乱的爱情,但是仍然不同于色情文学。前者致力于探讨人性的奥秘和人们面对情欲及其诱惑追求人性解放的多种空间与途径。后者则流于机械地展示性活动及其过程。莫达尔认为:“儿童幼时都有暴露和偷看的癖好。如果发展正常,会演变成强烈的表现欲和求知欲。作家若仍有这两种倾向,就会写出不正经的色情文学。”(20)依据他的观点,作家在作品中成为暴露狂,以发泄无法满足的冲动,产生的便是色情文学。但是爱情文学与色情文学的区分并不是绝对的,在一些优秀的爱情文学作品如《十日谈》、《忏悔录》中,也或多或少存在着暴露狂的倾向。
五、爱情与神性
爱情包含着灵与肉、沉湎与超越的悖论、人性与神性的抗争。自从柏拉图把爱情分为肉体之爱和精神之爱,追求不朽是爱情的目标,爱情被归诸于精神范畴,爱情与神性的冲突就不可避免。在基督教禁欲主义统治西方的中世纪,文学中提供了不少教士或信徒耽溺于性爱的例子。薄伽丘《十日谈》第三日写阿莉白要出家修行,遇着修道士鲁斯蒂科,鲁斯蒂科教她怎样把魔鬼送进地狱,却垂涎那少女的青春美貌,借着侍奉天主的名义,引诱她与自己发生性关系。现代仍然不乏描写本能欲望与宗教信仰之间的冲突的作品。法朗士的小说《泰绮斯》写的是道行深厚的神父巴弗尼斯原本试图用基督的教义感化美丽的妓女泰绮斯,但是当泰绮斯真的皈依宗教,到了修道院做了修女之后,巴弗尼斯却疯狂地爱上了泰绮斯,向垂死的泰绮斯表白他的爱情,他的欲望战胜了宗教的信念。
但是,基督教传统又隐含着爱情与神性的某种关联。比如在基督徒的婚礼中,婚姻便是对爱情的庄重承诺。新郎、新娘面对圣坛,由牧师宣告婚礼开始,祈求上帝的赐福,新郎、新娘在神和众人面前表明他们共结连理的心愿。这种仪式旨在使世俗的爱情神圣化,不仅表示恋爱双方彼此关心、疼爱,创造新的生命、新的经验,也表示在人生各种际遇中把爱心推及于无限。美国哲学家雅各·尼德曼写道,“无私之爱的能力是人性中的神性层面”,有“两种爱,一个是升华的,似乎远不可及;另一种则是沛然莫之能御,忘我、焦虑、喜悦、苦恼兼而有之。我们共同生活的方式是否可以创造出心中这两个世界、两个爱和两种人生之间的接触点?”(21)实际上,优秀的爱情文学正是试图回答他的这个问题,致力于创造尼德曼所说的两种爱、两种人生、两个世界的接触点。意大利作家德·亚米契斯的小说《卡尔美拉》就是如此。小说写的是距离意大利西西里岛70海里的一座小岛上发生的故事。岛上美丽的民家女卡尔美拉以西西里女子特有的狂野热烈地爱上前驻军中尉,二人发生了一段轰轰烈烈的爱情,却被始乱终弃,继而发了疯,一见到后来来岛的漂亮驻军军官便频频示爱,尤其对现任的驻军军官表示好感。该军官了解卡尔美拉的遭遇后,对卡尔美拉由同情而生爱情,试图医治好卡尔美拉的病,幻想着“那时,我会觉得自己就是造物主,我也能够创造出什么东西,我仿佛享有两个灵魂,拥抱着两个生命,我的生命和她的生命;我会觉得,我那造物是命运之神把她派遣到我的身边来的,我要把她像天使一样引见给我的母亲……”终于设法唤起了卡尔美拉的意识,收获了幸福的爱情。
我们可以超出基督教文化传统,从一般意义上看待爱情与神性的关系。对白头偕老的现世永恒之爱的追求可以视为世俗爱情生活中的神性层面。我们都记得奥维德《爱的艺术》中李雷克斯讲述的那则故事。众神之神朱比特和其随从化装成人来到一个繁华的村庄,但只有一户住在茅草和芦苇搭建的破旧房屋的一对老夫妻热情招待了他们。朱比特提出要报答他们的恩情时,这对穷困的老夫妻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让他们白头偕老,一同侍奉天神。从更高意义上说,爱情不仅追求被爱,更是一种无私的付出和默默的奉献,这种自我超越的层面更接近神性。有人曾经用“爱是人类惟一的救赎”来概括史铁生本人及其作品的特征,这自然包括他作品中的爱情描写。在史铁生笔下,爱情可以是一种冥思,一种悔悟,比如《务虚笔记》中医学院青年学生F爱上右派女儿N的故事。
可见,如同爱情自身包含着悖论一样,爱情文学也存在着悖论。一方面,爱情文学和文学中的爱情描写昭示了人类由动物性向人性到神性的演进,在此我们可以借用马斯洛另一重要思想“再圣化”来加以说明。“再圣化”要求我们不断地在生活中形成一个高峰,注意从生活的诗意的一面去看待它,寻求其神圣的、永恒的、象征的意义。(22)所以文学还会源源不断地创造出新的爱情梦想和爱情神话,启迪我们去发现和想象可能的人生。另一方面,爱情文学和文学中的爱情描写终归又显示出人类由动物进化而来的种种痕迹,本能与人性、人性与神性在此盘根错节,呈拉锯状曲折展开。乌纳穆诺说得好:“爱本身就是精神中的某些肉欲。由于爱,我们才得以了解:凡是精神必有属于它的实质的肉体成份……肉体爱的喜悦,创生的痉挛,就是一种复活的感觉,一种在别人身上更新自身生命的感觉……既是受难的肉体,它必得受苦,藉此而得永生。”(23)如何更好地面对本能、体验人生、重塑人性,文学做出了最为多姿多彩的回答。
参考文献
[1]莫达尔:《爱与文学》, 郑秋水译,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 1987年, 第17—18页。
[2]弗洛伊德:《爱情心理学》, 滕守尧译, 见《性爱与文明》,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6年, 第203页。
[3]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 高觉敷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4年, 第9页。
[4]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9年, 第119页。
[5]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4年, 第435页。
[6]马斯洛:《人的潜能和价值》, 林方主编, 北京:华夏出版社, 1987年, 第368页。
[7]司汤达:《十九世纪的爱情》, 刘阳等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年, 第7页。
[8]柳鸣九:《人性的观照——世界小说名篇中的情态与性态》,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8年, 第143页。
[9]弗洛伊德:《性学三论》, 见《文明与缺憾》, 傅雅芳等译,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6年, 第21页。
[10]蒙哥马利.海德:《西方性文学研究》, 刘明等译, 海口:海南出版社, 1988年, 第32—33页。
[11]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 洪佩郁、蔺月峰译, 重庆:重庆出版社, 1990年, 第131页。
[12]恩格斯:《格奥尔格.维尔特》,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5年, 第9页。
[13]劳伦斯:《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辩》, 见《劳伦斯散文》, 黑马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8年, 第263—264页。
[14]弗洛伊德:《爱情心理学》, 滕守尧译, 见《性爱与文明》, 第217页。
[15]福柯:《性经验史》, 佘碧平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年, 第5页。
[16]夏志清:《夏志清文学评论经典——爱情.社会.小说》, 台北:麦田出版社, 2007年, 第19—20页。
[17]潘一禾:《裸体的诱惑——论文学中的性与情》, 深圳:海天出版社, 2002年, 第218、246页。
[18]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 第266—267页。
[19]略萨:《谎言中的真实——巴尔加斯.略萨谈创作》, 赵德明译,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7年, 第68页。莫达尔:《爱与文学》, 第129页。
[20]莫达尔:《爱与文学》, 第129页。
[21]雅各.尼德曼:《爱情书》, 杜默译, 台北:智库股份有限公司, 1997年, 第39—50页。
[22]参见马斯洛:《人性能达的境界》, 林方译,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7年, 第57页。
[23]乌纳穆诺:《生命的悲剧意识》, 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 1987年, 第85—87页。